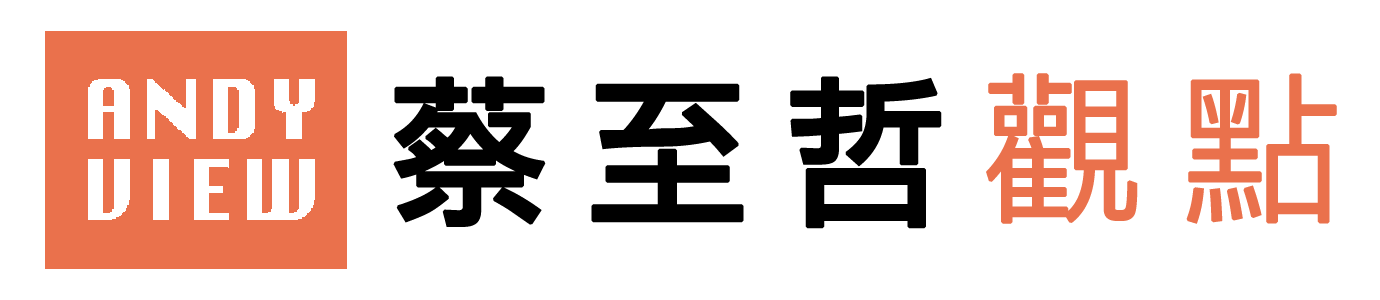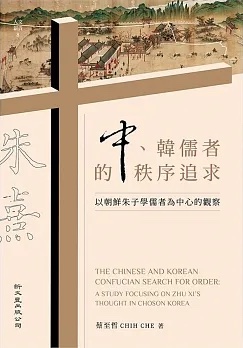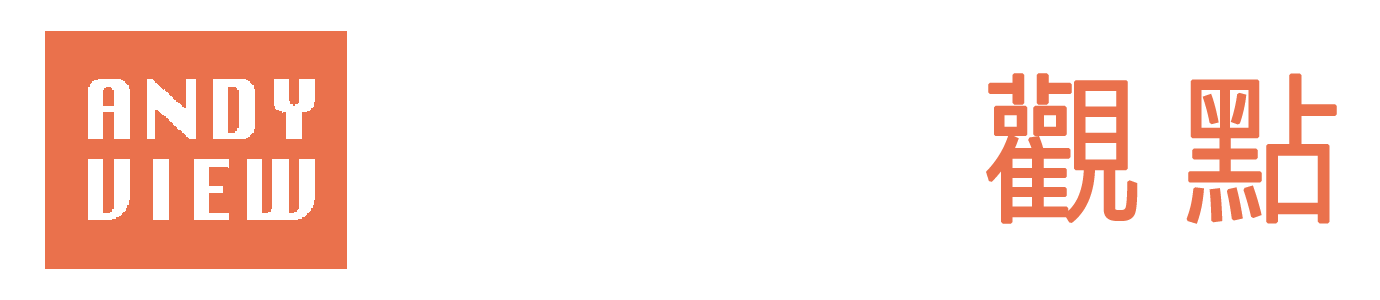
內容簡介
本書以東亞儒學視野,參考沃格林(Eric Voegelin, 1901-1985)之研究,思考朱子學秩序關懷裡的價值與界限。朱熹道統思想對傳統漢唐中華秩序進行批判,類比沃格林思想,可視為一種中華秩序下的「存在的飛躍」。朝鮮儒者在明中葉至明清鼎革的巨變與失序危機感中,希冀傳承「朱子之後」的道統,重塑中華秩序,類比沃格林思想,也可視為一種中華秩序下的「存在的再飛躍」。值得我們在今日反思何為「中華秩序」之時作為參照。(人文新貴8)
作者介紹
蔡至哲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畢業,同時讀政大宗教所博士生。曾任中研院文哲所博士後研究員,現任臺師大東亞系博士後研究員,臺大兼任助理教授。學術關懷在東亞儒學、基督宗教史,發表過不少相關中英文論文,曾譯《理性的勝利:自由、科學、資本主義,以及進步的理性神學》。
目錄
序一/吳展良
序二/張崑將
第一章 東亞儒學與秩序研究的可能
第一節 前言:中華秩序正在恢復?
第二節 從去除「單一中心」的東亞儒學研究
第三節 沃格林的秩序研究對東亞儒學的啟發
第四節 東亞儒學的秩序研究回顧
第五節 東亞儒學的秩序符號:三代、聖人、道統
第二章 本末一貫──再探朱熹的《大學》秩序關懷
第一節 身處北宋亡國與秦檜主政陰影下的朱熹
第二節 儒學本末思維的歷史脈絡
第三節 朱熹對「一貫之道」與「本末思維」的連結與詮釋
第四節 朱熹的政治論述:本末一貫的《大學》之道
第五節 「道統」與「三代VS漢唐之辯」的歷史哲學意義
第六節 結語
第三章 朝鮮王朝君臣對明代中華秩序的接受與抗拒
第一節 事大政策下的朝鮮王朝君臣
第二節 朝鮮儒者對明代中華秩序的批評
第三節 中國之法有不可法者:朝鮮儒者對明代中華政治秩序的駁斥
第四節 許稠批判明代中國「時王之制」在朝鮮的後續影響
第四章 朝鮮王朝君臣對宋代中華秩序之嚮往
第一節 朝鮮王朝的中華秩序觀研究回顧
第二節 「後三代」之首:宋
第三節 朝鮮儒者的宋代嚮往:三代之治再現於朝鮮
第四節 朝鮮君主的宋代中國歷史分析:以文化力量為依歸的判準
第五章 秩序危機與朝鮮朱子學的深化
第一節 朝鮮道學儒者初次執政:趙光祖的得君行道
第二節 己卯士禍:朝鮮道學儒者「外王」行動的挫折
第三節 士禍與朝鮮道學的秩序危機
第四節 李滉對朝鮮朱子學的向內深化
第五節 公患道學失傳:雙重秩序危機下的退溪思想
第六節 朝鮮儒者對儒學道統中心的轉移之詮釋
第七節 五賢之卓立:朝鮮儒學道統系譜的建立
第八節 結語:朝鮮中華秩序與存在的再飛躍
第六章 再失序:朝鮮道學與黨爭
第一節 朱熹的〈與留丞相書〉在南宋以降中國的流傳
第二節 對經典的政治性解讀:李珥對〈與留丞相書〉的應用
第三節 朝鮮宣祖對李珥的肯認與〈與留丞相書〉的典範化
第四節 朝鮮王權對朱熹〈與留丞相書〉的挑戰
第五節 道學政治的失序:朝鮮黨爭的激化
第七章 朝鮮的儒耶交流與秩序的再探索
第一節 秩序關懷與儒耶交流
第二節 朝鮮黨爭與「妬忌」問題
第三節 朝鮮王朝「尚閥」與儒者歸信天主教的關聯
第四節 耶穌會士對儒學「克己」思想的詮釋
第五節 李瀷對龐迪我「克妬」思想的詮釋
第六節 奉教儒者對「三代」符號的再詮釋
第八章 結論──朱子學秩序關懷的價值與界限
第一節 道統傳承VS十全武功:朱子學對秦漢式中華秩序的反省
第二節 本末一貫秩序關懷的僵化與限制:緊張性的喪失與不寬容
參考文獻
附錄 本書初稿(博士論文)摘要
後記
序一/吳展良
我與蔡至哲君相識多年,深知他對於東亞世界的歷史、政治暨其學術文化,一直抱有濃厚的興趣,對於儒學與朱子學,尤其有特別的研究。蔡君相信東亞文化需要從跨國家與多元的角度來認識,而朱子學代表著近世東亞文化的最重要共通基礎,他是以決定以朝鮮朱子學為主要研究對象,尤其著重於學術思想與政治之間的關係。經過長期的奮鬥,他不僅獲得博士學位,而且在過去的短短幾年間,於重要期刊(THCI)先後發表了八篇文章,誠可謂難能可貴。他的博士論文從中、韓儒者「秩序追求」這一角度,深入探討了朝鮮朱子學在韓國歷史上的政教意義。讀者眼前這本書就是從其博士論文改寫而成,其中絕大多數篇章均已在重要期刊發表。
比起他同輩的學人,至哲是一箇敢於問大問題,並努力從一些直扣根本的角度去處理這些大問題的研究者。在本書中,他問了一些攸關整個東亞世界的政治與社會文化秩序的關鍵問題:近世東亞世界的政治與教化的秩序基礎為何?中華秩序是否正在恢復?在漸行漸遠的東亞世界,當如何去認識儒學與朱子學?思想、秩序與歷史的關係?而他最核心的問題,應是以宋代朱熹的道統觀為代表的東亞傳統世界秩序,如何既具有超越國別乃至現實政治的影響力,又還能保持一定的公開性與開放性?也就是既能幫助建立普遍秩序與公義,卻又保持多元發展的潛力?
除了大量繼承臺灣、大陸與韓日的東亞儒學研究傳統,本書還運用了德國學者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 1901-1985,下圖)對「歷史與秩序」之關係的探討,尤其是他的「存在的飛躍」觀及東西比較研究。這使得他對於宋代朱子學所具有的某種「超越性」價值,及其在歷史中建立秩序的方式,獲得了許多新的見解。但他同時也體認到「以西方現代的世界觀與語言來批判或重新詮釋傳統雖然產生極多的創獲,流 弊亦甚多」。是以他的文章依然聚焦於「主導前人生活與心靈活動的許多基本理路」,以「更認識或貼近古典文明的心靈」, 並主要以中國與朝鮮儒學為研究標的,企圖超越過去「殖民地化」或「民族主義框架」下的歷史觀與研究。
為達成上述目標,他嘗試從東亞歷史自身出發,重探曾作為整個東亞世界政教秩序基礎的中國宋代世界觀的歷史內涵,及其對朝鮮的影響。他發現歷史上「朝鮮王朝君臣(從正祖朝開始)對宋代中國的歷史表現出高度嚮往之心態」。他們拒絕部分明代的中華秩序,並不斷將自身立國等同於「宋代中華秩序」再現。他本此觀點重探朝鮮儒學,尤其是宋學與朱子學所曾具有的普世性價值,及其在朝鮮「去脈絡化與再脈絡化的歷程」。其研究不僅對東亞儒學史與韓國史別具意義,也具有比較文明史及文化交流史的意義。韓國朝鮮王朝時期,君臣有關宋史、宋學的研究與論述極多。他企圖據此探索「宋代政治文化與思想在朝鮮儒者再脈絡化的歷程與結果」,以研究朝鮮儒者如何運用中華秩序觀。不僅如此,本書 還探討了末期的一些朝鮮儒者如何在上述基礎上與基督教對話,以「尋找重建秩序的出路」。朝鮮儒者曾先以宋代中華秩序為藍圖,建立了「朝鮮中華秩序」;到了後期面對西方的挑戰,「則轉以宋中後期或宋末危局來與朝鮮對比,藉此針砭朝鮮國事」。透過了韓國經驗,以及這種跨國家文化的研究,我們更可以認識曾作為東亞世界秩序基礎的中華秩序之特質、困境與出路。這在中國重新崛起,中西政教體系重新對峙的今天,尤其富有特殊的意義。
蔡君一向興趣廣泛,他曾深入研究韓國儒學、中國儒學、基督教,也曾探索文藝復興、以色列文化、西方人文學思想等各類主題。他對文明交流史與比較文明的研究深具興趣,也一直不斷地在思考與探究東亞文明的發展道路及其與西方現代文明的關係,尤其聚焦於東亞政教秩序的基本特質與發展這一重大課題。本書研究所得的很多觀點,都深具開創性與重要性。這些年來,蔡君忠於自己的志趣,堅持探讨這些鮮為學界所思考的重要議題,並保持了強大的研究與寫作熱情。在他的新書出版之際,我很樂意特別為之推薦。
臺大歷史系教授
序二/張崑將
東亞儒者對「秩序追求」的鄉愁
《中、韓儒者的秩序追求──以朝鮮朱子學儒者為中心的觀察》是至哲的博士論文,現在經過徹底改寫後,終於要問世了。我忝為他的口試委員之一,但並不是口試時間才看他的論文,而是在論文撰寫的漫長期間裡,至哲經常來拜訪我的研究室,一同討論他的寫作收穫,從中我也對朝鮮儒學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堪稱教學相長。如今這本博論要出版,承其好意,要我寫序,推辭再三,盛情難卻。
至哲本書探討的內容堪稱國內少有,國外亦不多見,不僅具有東亞的跨域比較視野,也涉及東西文化的比較。如實言之,要真切地結合這兩項比較,對任何研究者而言,都是相當大的挑戰,但至哲勇於接受挑戰,確實找到當代相當好的「秩序」理論作為切入點,企圖結合當代美國傑出政治哲學家沃格林(Erich Hermann Wilhelm Vögelin)的秩序理論,來貫穿與比較近代以前東亞儒學的政治秩序的發展,希望找到一個東亞儒者追求秩序的趨勢與轉化。因此本書透過一些儒學共通的關鍵性詞語概念如「道統」、「三代」、「本末」、「一貫」,再配合朝鮮政治脈絡中的黨爭與士禍,並結合明清鼎隔前後的政治與文化的巨變,再將之脈絡化於中國與朝鮮儒者的政治與文化關懷,釐清一個道統由中國轉移到朝鮮的過程,其實也就是政治秩序與文化秩序轉移的過程,並將朝鮮定位為傳承「後朱子時代」的道統,在明清鼎革的歷史巨變之際與失序危機感中,重塑了以道統為依歸的中華秩序。當然,這個中華秩序愈趨向近代,就愈接受嚴重的挑戰,諸如天主教及西方文明之挑戰,在至哲書中第七章也充分被分析出來。
以下我想從東亞儒學的視野,引導讀者進入至哲本書核心課題中的「秩序追求」。近代以前,儒家文化曾經深刻影響了中國周邊國家的韓國、日本及越南,學者稱「東亞教育圈」或「漢字文化圈」,皆有深刻的儒學教育、養士教育及成聖教育的內涵。相較於越南與日本對儒家文化的吸收,朝鮮儒者堪稱最為深入,並且深入到骨髓,導致有所謂「道統在朝鮮」的中華正統意識。至哲此書的焦點也是放在朝鮮儒學,並聚焦於「道統」這個有關「秩序追求」命題的渴望。「道統」涉及的層面,可簡化兩個面向,一是文化認同,一是政治認同,以下我擬從韓日越三個國家知識份子各有一段討論「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的史料中,帶領讀者進入至哲這本書所探討有關「秩序追求」既多元且活潑的面向。
- 朝鮮:李恒老(1792-1868)
西洋亂道最可憂。天地間一脈陽氣在吾東,若幷此被壞,天心豈忍如此?吾人正當為天地立心,以明此道汲汲如救焚。國之存亡,猶是第二事。
- 德川:山崎闇齋(1618-1682)
嘗問群弟子曰:「方今彼邦,以孔子為大將,孟子為副將,牽數萬騎來攻我邦,則吾黨學孔孟之道者為之如何?」弟子咸不能答,曰:「小子不知所為,願聞其說。」曰:「不幸關逢此厄,則吾黨身披堅,手執銳,與之一戰而擒孔孟,以報國恩,此即孔孟之道也。」
- 越南:《皇越春秋》
太祖大怒,命推出斬之,武士牽黃福出,忽見黎公僎抱住,少碍向前稽首,請代尚書,太祖曰:「我殺寇讎,公何救解?」少碍奏曰:「臣與公僎本受業尚書,方生獲時,師生之誼,釋之亦宜,第念君臣之道,不敢狥私,故解回稟納,臣請自代,死亦無憾。」
首先,我們看第一則有關朝鮮末期衛正斥邪派儒者李恒老(左圖)的論點,背景是處於西方軍事及宗教勢力侵擾朝鮮之際,為了捍衛儒學正道命脈,竟喊出「國之存亡,猶是第二事」,將文化認同放到政治認同之上,這在現代人看來,有點百思不解。
第二則的歷史背景是正值清帝國滅了明朝後,掀起日本國上下的震撼,擔心蒙古侵日的「元寇」事件又將重演,而這位德川時代奉朱子學甚勤的儒者山崎闇齋竟有這樣的設問,如果孔孟為帥,來攻打日本,將一戰擒孔孟以報日本國恩。第三則是越南史料,引用的是《皇越春秋》,這部書是類似《三國演義》的歷史小說,引文中描述的是明成祖時期曾將越南收歸帝國版圖,派遣一位黃福(1362-1440)擔任交趾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兼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類似殖民地時代的總督,但這位黃福勤政愛民,贏得越南人上下的愛戴,在其去職後,繼任者貪暴無道,越南人乃掀起獨立復國的戰爭,黃福復被派往平亂,過程中黃福被越南復國首腦黎利(1385-1433,後來的黎朝太祖)所俘虜,在欲斬殺的過程中,被昔日教導過的越南學生少碍、公僎求情,願意代師受死,黃福不僅免死且被尊嚴地對待。
現在,我們從上述三段論述,比較三國有關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之間的微妙關係差異,這也反應出三國對「秩序追求」的同異關係。我簡略用以下三關係來凸顯三國面臨中華秩序在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的差異,即越南是「師弟關係」,朝鮮則是「父子關係」,但日本則是「養父子關係」。越南的「師弟關係」所展現的認同是,即便政治上獨立,但仍無法斬斷與割捨那個「文化認同」之情,師弟之間聯繫的是文化情感。熟悉越南的歷史都知道,越南古代開國神話也須遠溯自中國的神農之後,長期以來也是中國的朝貢國,在獨立以前即不斷吸收中國儒學文化,《皇越春秋》裡所凸顯的師生之情,是難以割捨的文化情感。其次,日本的「養父子關係」則是為了政治認同,可以斬斷或割捨「文化認同」,對日本而言,政治主體是日本,文化主體可以從「養父」的中國置換回親生的「日本文化」,這中間可以毫不疑惑,故未如越南還存有「師弟情懷」。至於朝鮮的「父子關係」,則是在政治上與文化上均無法與中國切割,政治上與中國的緊密朝貢關係比越南有過之而無不及,文化上又是公認的儒學模範生。尤其在豐臣秀吉侵略朝鮮的「壬辰倭亂」(1592-1597)戰事不久,許多朝鮮儒者視明帝國為「父母國」,故稱為「父子關係」實不為過。
不過,我們還得追問,為何會有這樣的差異?這不得不讓我們從地理關係的遠近來探索這個差異的根本原因,因為地理遠近關係充分可以說明中心與周邊之鬆緊關係。朝鮮、越南是和中國處於緊密的「周邊關係」,而日本和中國則是處於鬆弛的「亞周邊的關係」。換言之,地理愈接近中國者,其政治與文化的關係愈是斬不斷的連接關係;而地理屏障愈深者,愈有脫離中心呈現自己的政治與文化主體,日本屏障是一海之隔甚於韓、越,而越南有崇山峻嶺之屏障則甚於僅一江之隔的朝鮮。因此,呈現由近而遠的「父子關係」、「師弟關係」到「養父子關係」,也可以從地理遠近關係窺出端倪。
我們還可以深問:「一戰擒孔孟」的設問在朝鮮與越南的文獻不會有,而「國之存亡,猶是第二事」之論唯獨朝鮮國度才有。因此,值得推敲的是「此國有,彼國無」或可窺探韓日越三國吸收儒學的深淺程度,或是用至哲這本書所關心的對「中華秩序的追求」之渴望程度,也一樣適用。由於至哲本書關注在朝鮮儒學,以下我們聚焦朝鮮儒學繼續深入這事實上,李恒老的「國之存亡,猶是第二事」,並非孤鳴先發,早在丙子胡亂之際(1636-1637)金人威逼朝鮮必須放棄承認明帝國為宗主國,改奉清為宗主國,當時朝鮮君臣上下曾經出現過「明大義」與「存國體」的激辯抉擇,若要「明大義」就等著國家被金人消滅,若要「存國體」則須拋棄兩百多年來明朝對朝鮮的「大義」。顯然,李恒老「國之存亡,猶是第二事」所面臨秩序追求的緊張性,只是十七世紀初期的延續課題。另外,李恒老的「國之存亡,猶是第二事」不禁讓我們連結到晚明時代的顧炎武(1613-1682),他面臨國破家亡也喊出:「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換言之,對儒者而言,「亡國」與「亡天下」的差異,在於儒者的文化認同的「天下胸懷」高過政治認同的「國家民族」,用至哲這書所關懷的朝鮮儒者對秩序的追求,就是「道統」高過「政統」,我將朝鮮儒者對「道統」的堅持心態,姑稱為「鄉愁」(nostalgia)。
「鄉愁」約有兩種心態,一種是離心力的鄉愁,雖有原鄉情懷,但最後勇於做自己,甚至做出如哪吒一樣割骨還肉之舉,日本對中華秩序的「初迎後拒」的情況就屬這類。另一種是向心力的鄉愁,帶有濃濃的懷鄉情懷,難以做出切割,不過這種向心力往往又帶有「近鄉情卻」之複雜心境,朝鮮與越南對中華秩序的「既迎又卻」,可說是這種鄉愁的展現。不過,朝鮮更發展出「道統」的鄉愁,這是日本與越南兩國所比較沒出現的文化現象。質言之,能說出宋代朱子以後無真儒,而朝鮮出現大量真儒,大概只有朝鮮儒者有這種氣魄與承擔。唯有真儒方能承接「道統」,中國實已無道統,故道統悄然地「轉移」到朝鮮,這就是朝鮮儒者對道統的鄉愁,既深刻又複雜,既難言又豐沛。這也是至哲此書關心的核心課題,讀者若能耐心讀完,或許比較能掌握朝鮮儒者的心境。以上的比較中國周邊國家對「秩序追求」的離心力與向心力之類比,希望有助於讀者進入至哲這本書以中韓儒者對「秩序追求」之探討核心,我的導讀只是淺嚐即止,且是從外部的比較方式,至於至哲書中裡面的詳盡探析與精彩內容,需要讀者進一步探驪得珠。
當然,所有歷史都是當代史,至哲本書所關心的「秩序追求」也不例外,故一開始就問「中華秩序正在恢復嗎?」現在西方的衰弱與東亞的崛起(特別是中國的再興)的國際局勢,已是不爭的事實。至哲書中關心的中韓儒者「中華秩序」是千古東亞儒教文化圈的共同命題,中華秩序過去稱「天下秩序」,而其核心關鍵在「道統」。這個「道統」曾在東亞儒教圈中產生重大的作用,除了中國本身有儒學的道統堅持外,還有兩個國家曾經迷戀過這個儒學的道統,一個是本書關注的朝鮮王朝,另一個則是臺灣的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抬出道統,不足為奇,畢竟與中華同文同種,面對國共對立,蔣介石統治的中華民國宣稱自己中華文化的正統性,以對抗對岸奉馬列主義為主的共產中國。但是,朝鮮與中國並非同文同種,這個國家與民族為何那麼堅持儒學的道統,並且因為信奉朱子學,信得比中國明清王朝還更朱子學,朱子學幾乎成為朝鮮的國教,並且他們深信道統也轉移到了朝鮮。可見,「道統轉移」的秩序追求課題,從過去到今日都還是個討論「熱區」,尤其在中國再興之際,不遺餘力地恢復中華文化,下一波的「道統轉移」是否能如至哲引用沃格林所說的「存在的飛躍」,值得令人拭目以待。是為之序。
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教授 張崑將 2021/06/24
前言:中華秩序正在恢復?
21世紀東亞與世界面臨到所謂「中國崛起」的課題。中國的傳統文化與所謂的「中華秩序」受到不少學者重視。美籍日裔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探討政治秩序的起源時,就認為從國家建構的角度而論,中國的重要性更勝過希臘、羅馬,因為「只有中國創造出韋伯(Max Weber,1864-1920)所定義的那個現代國家」;也是「世界上最早設計出理性的、從功能角度組織的、以不講私人關係的取材、升遷標準為基礎的行政體系,也就是好政府」。
某段時間,部分臺灣學者對「中國崛起」充滿好奇也樂觀其成,朱雲漢顛覆了傳統的刻板印象,認定中國的體制在「一黨專政」的外衣下,有强大的治理能力與政治穩定?既有中央集權的決策明快,又有類似「聯邦制」在各省的因地制宜與試驗創新?他認為,中國充分發揮了「大」的優勢與「後發優勢」?所謂的「中國夢」在這些學者的眼中,簡直有可能成為二十一世紀人類文明的重要道路與參照?也讓世界秩序正在重組?
隨著近年來國際情勢的轉變,也有不少學者開始對所謂「中華秩序」的恢復進行批判。王飛凌認為,「中華秩序」就是「中華世界帝國秩序」,是一種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甚至是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的世界政治秩序,奠基於用儒學粉飾其表的法家帝國政體(即秦漢政體,Qin-HanPolity)之上。王飛凌整理了中華秩序的幾個主要特徵:總體性(totality)、普世性(Universality)、等級性(hierachy)、多重性(dualities)、控制欲(control)、虛偽欺騙和表裡不一(hypocrisyandduplicity)等等,對傳統中華秩序提出諸多批判,也對當前所謂的「中國崛起」提出警告。
王飛凌認為:「中國夢裝腔作勢的要把19世紀以前的中華秩序(長期的停滯與專制)重新包裝,作為『西發里亞體系的替代方案』,宣稱自己是『另類現代性』,但其實只是另一種形式的帝國主義而已。」王飛凌的研究可謂是對當前新一波中、美貿易戰、新冷戰開始後的一種反中思潮的呼應。
對中華秩序的分析,存在如此不同的兩極論點。除了因為政治立場與利益衝突的對抗外,是否能有更寬廣的視野重新去思考,不再只有對抗的兩極立場?也許透過嘗試回到歷史不同時空裡的「何為中國?」「中國要如何被論述?」會對當代僅以民族國家、現實政治立場的思考有所補充與幫助。
正如歷代中國與東亞各區域之間的「文化中國」與「政治中國」的撕裂及其辨證,顯現了「中國」或「中華」概念在東亞區域絕非鐵板一塊;也有如往昔史華茲(BenjaminSchwartz,1916-1999)曾以「追求富強」一說去詮釋中國現代學術與思想史的核心關懷,已經受到重新檢討,也就是即便身處清末民初的知識份子,已經面臨類似「全盤西化」的挑戰,卻仍帶著傳統儒學的思維模式在處理中西文明交會的深層問題,可見超脫現代學術的世界觀對研究傳統東亞的重要性。加上擴大視野到東亞,也許可以讓我們從古代不同世界觀的思想資源中,找到對當代議題的啟發。
摘要
本書以東亞儒學視野,參考沃格林(EricVoegelin,1901-1985)的秩序研究,關注中、韓儒者之思想,特別是朝鮮朱子學之發展,藉以思考朱子學秩序關懷裡的價值與界限。朱熹透過區別1.「三代」(上古三代);2.「孟子死後的漢唐千五百年間」;3.「二程及朱熹自己所處的宋代」。建立了「道學」的歷史觀,讓「道學」站在更高的高度去批判漢、唐的失序。沃格林曾定義西方歷史上所謂「存在的飛躍」就是與原有帝國秩序的決裂,走向了分殊的秩序。朱熹以道統的高度,對傳統漢唐中華秩序進行批判,可類比沃格林思想,視為一種中華秩序下的「存在的飛躍」。
然而,傳統東亞秩序強調一元性、整體性、政教合一的特質,若溯其根源,也與朱熹高舉《大學》的「貫穿本末」,全面恢復秩序的思維,有其深刻關連。對近世東亞儒學之發展更有深遠影響。明清兩代皇權以全面掌握秩序之名,將「道統」的話語權篡奪,使統治者變成「政治」、「文化」無上的權威。實質上否定了朱熹思想的緊張性與對皇權批判反省的可能。當全面恢復秩序的企圖,喪失了對真理的不確定感與緊張性,而代之以如沃格林所說的靈知主義式的不寬容與壓迫,反而帶給人更多關於秩序的困惑與憂慮。
朝鮮儒者希冀傳承「朱子之後」的道統。在明清鼎革的歷史巨變之際與失序危機感中,重塑了以道統為依歸的中華秩序。類比沃格林思想,可以視為一種中華秩序下的「存在的再飛躍」。值得我們在今日重新反思何為「中華秩序」之時作為參照。1945年以後的中華民國在臺灣,使中國歷史發展往文化傳統與民主自由理念去接枝,也如同對中華秩序進行了再創造。即便經過了所謂「去中華」後,透過深化民主、保護、尊重多元價值與信仰,重新詮釋傳統,最終可以不同的樣貌「再中華」。